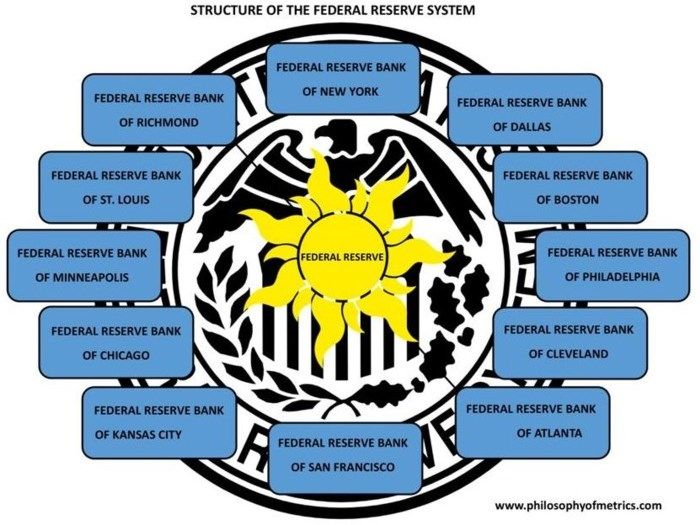
|
| 美国从小布什总统任内,国家债务便年年快速上升。 |
中评社╱题:余英时的“帮派”与“典范” 作者:黄光国(台湾),台湾大学荣誉教授
【摘要】在当时的美国,“哈佛帮”的理论是代表主流价值的“常态科学”,反战学生的观点,则是必须被设法“摆平”的“异例”。更清楚地说,由于常态科学是由某种典范所宰制,典范总是受到绝对的信赖。但它与实践结果之间,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“异例”。“常态科学”的主要工作,便是经过恰当的调整,来解决这些反常的异例,以使典范不受损害。
一、红学研究的“典范”
龚忠武在〈辛丑元年祭〉的长文中,叙说他跟余英时之间“亦师亦友”的关系:1966年,他从台大到哈佛,成为费正清门下的一名研究生,余英时正好从密西根大学转聘到哈佛,为罹患严重精神病的杨联升代课。两人除了师生关系之外,周末还经常到他家打牙祭,并参加围棋俱乐部的棋会。在1968年-1969年,余氏祇是个在哈佛代课的助理教授,在哈佛的去留问题,成为他最大的心理压力,一度情绪十分消沉,香烟不离手,藉烟消愁,并且不讳言,可能回到香港教书。
1969-1970年之交,海外留学生爆发了保钓运动,龚忠武发现:余氏在校园里老跟在费正清后面,做说服反战学生的工作。余氏是围棋高手,两人闲聊时曾对龚忠武说:棋如人生。他现在正为他今后的学术生涯,下一盘大棋。
从1970年起,正值中壮年的余氏,为了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而拚命著书立说,企求扬名立万。在这段期间,余英时完成了有关《红楼梦》研究的三篇文章,一起收录在《历史与思想》一书中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篇〈近代红学的研究与红学革命〉(1974),余氏引用孔恩(Thomas Kuhn, 1922-1996)在其名著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中所提出的“典范”之说:
“典范”可以有广狭二义:广义的“典范”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、价值、和技术(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, value, and techniques),因此又可称为“学科的型范”(disciplinary matrix)。狭义的“典范”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(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)。这个狭义的“典范”也是“学科的型范”中的一个组成部分,但却是最重要、最中心的部分。
在这篇文章中,余英时认为:红学研究史上出现过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互相竞争的“典范”,第一个“典范”可以蔡元培的〈石头记索隐〉为代表,其中心理论是以《红楼梦》为清初政治小说,旨在宣扬民族主义,吊明之亡,揭清之失。第二个“典范”认为: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,此说起源甚早,直到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问世,才成为一种新的“典范”。
对于科学哲学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:孔恩所说的“科学革命”是指“自然科学的革命”,他并未提到“人文学”是否适用此一概念。“红学研究”中,不管是“索隐派”也好,或是“考证派”也罢,其实都是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余绪,跟孔恩所说的“科学革命”并不相干。
余英时在提出他的“红学革命”说时,不用他最崇拜的柯灵乌历史哲学,反而非常勉强地采用孔恩的“科学革命论”,很可能是因为他注意到孔恩有关“常态科学”的主张:
孔恩的研究充分显示一切“常态科学”(normal science)都是在一定的“典范”指引之下发展的。科学家学习他的本门学科的过程,通常并不是从研究抽象的理论和规则入手。相反地,他总是以当时最高的具体科学成就为楷模而逐渐学习得来的。这种具体的科学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书的方式出现的:在以往则见之于科学史上所谓经典的作品,如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(Aristotle′s Physica)、牛顿的原理(Newton′s Principia)等等。
科学史上树立的“典范”的巨人一般地说必须具备两种特征:第一、他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,并且在这种成就还起着示范的作用,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进。第二、他在本门学术中的成就虽大,但并没有解决其中的一切问题。恰恰相反,他一方面开启了无穷的法门;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无数的新问题,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(即所谓“扫荡工作”mop-up work),因而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传统。
在《历史与思想》一书的“自序”中,余英时很清楚地表明,他最大的心愿是“明天人之际,道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成为科学史上树立“典范”的巨人。他十分明瞭:不管“红学革命”在学术上有多重要,他再努力搞“红学研究”,都不可能成为树立“典范”的巨人,他必须另辟蹊径。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,他要如何找出自己的“道”?
二、“现代化理论”的典范
依照孔恩的理论,科学社群(scientific community)是指在某一科学研究的领域内,探索目标大致相同的科学工作者。在常态科学阶段,科学社群通常会信仰同一个典范,接受同样的教育,拥有共同的语言,运用同样的方法,探索共同的目标。科学社群是连接个别科学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桥梁。科学家个别的发现,必须经过科学社群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产生互动。这也是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学者要加入某一科学社群,从事研究,必须从研究其典范入手。他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,可以这套共有的典范为基础,信守同样的研究规则及标准程序。这种信守的态度以及因而产生的共识,是常态科学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。任何科学研究的领域,都必须产生研究典范,才能从事进一步的研究,这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趋于成熟。
在哈佛思索他个人去留问题的时候,余英时必然已经注意到:哈佛大学的科学社群正在努力建构“现代化理论”(modernization theory)的研究典范。他们用二分法,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“传统”和“现代”两大类,美国是全世界“现代化”的领头羊,全世界文化变迁的大方向就是“现代化”,由他们的文化传统,朝美国的方向转变。
当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英克勒斯(Alex Inkeles,1920-2012)可以说是为“现代化理论”树立“典范”的巨人。他还设计出一种“个人现代性量表”(individual modernity scale),广为非西方国家所采用,我在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念书时,在杨国枢教授指导下所完成的硕士论文〈个人现代性程度与社会取向强弱〉,都采用了他所创立的研究“典范”。
英克勒斯精通俄文,二次大战期间,他曾经为美国情报单位工作,任务就是解读苏联出版品及广播中的重要讯息。在冷战时期,英克勒斯本人的研究主题却是苏联的社会变迁。他本人的著作也大多与此有关。建构“现代化理论”,并不完全是出自学术目的,更重要的是要配合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政策。
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(John. K. Fairbank, 1907-1991)的背景也类似于此。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。1941年,他被美国情报协调局征召,担任情报研究及分析工作;1942至1943年间,他以战略情报局官员的身分,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。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,并于1955年成立主持“东亚问题研究中心”。
依照孔恩的理论,常态科学时期,科学家的主要活动是在一套固定的科学标准下,将心力集中在特定的范围,精炼典范,加速科学的进步。科学研究中的解谜活动,其答案经常是在预期之中的;解答常态问题,通常祇是用一种新的方法达到预期的目标。这样的工作必须超越各种观念上的、研究方法上的或研究工具上的障碍。在内容上和在时间上,常态科学都占据了科学活动很大的部分。这时候,科学家的主要研究动机在于他相信:祇要我够高明,就必定有解答。
在1970年代,余英时既然已经下定决心,要留在哈佛并“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”,于是回到柯灵乌的历史哲学,集中全力,用他“先验的想像”,建构出他的核心理论“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”。这时候,有没有人觉察到他这种“历史的建构”方式有问题呢?有的。这个人就是和他有“亦师亦友”关系的龚忠武。
三、“哈佛帮”的危机与中国学
龚忠武《在哈佛的激情岁月》一文指出:
1968年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许多美国大学生深深感到,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:过去他们深信不疑的美国基本价值、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、政学关系、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,现在都面临信任危机,都需要彻底从新审视。一时之间,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突然变得一无是处,都出了问题!
他们的基本理念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,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,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,不值得美国人花钱,让美国青年去送命!他们基于学者的良心,一定要坚决反战。他们从理论上分析:导致美国陷入越战泥沼的原因,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,是美苏两极僵硬的反共反华冷战思维,是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。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,就是围堵中国理论的主要构成部分!
从孔恩的理论来看,这时候“哈佛帮”建立的理论已经面临了“危机”。然而,在当时的美国,“哈佛帮”的理论是代表主流价值的“常态科学”,反战学生的观点,则是必须被设法“摆平”的“异例”。更清楚地说,由于常态科学是由某种典范所宰制,典范总是受到绝对的信赖。但它与实践结果之间,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“异例”。“常态科学”的主要工作,便是经过恰当的调整,来解决这些反常的异例,以使典范不受损害。
当时龚忠武的反战同学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学报(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)和“哈佛校报”(the Harvard Crimson)上,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尔(Ezra F. Vogel)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。
1968年10月间,辩论的焦点,是质问费正清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,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?他们认为,这根本违反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,是可忍,孰不可忍?费正清被迫回应说,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,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,并且可以从中央情报局获得机密资料!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“中国学”的真实面貌!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祇是幌子,“中国学”骨子里祇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,是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,如此而已!
龚忠武说,当他知道这些事实,他的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;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、大方向和前景,不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。“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、失落、焦虑,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,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,适成鲜明的对比。我的哈佛之梦,开始幻灭了!”
|
